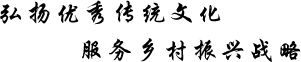目录
五、考证
琅琊山名来源的探讨
韩枫
琅琊山名的由来,自唐宋至今,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因西晋琅邪王司马伷而定名;二是因先任琅邪王后来当上了东晋元帝的司马睿而定名。
对这两种说法,清代、民国和当代的史志学者、地理学者,在编纂“琅琊山”条目时,采用了不同的记载方法。有的采用了两说並存;有的只记因晋元帝司马睿到此而定名这一种说法,有的认为司马睿到过琅琊山的说法不可信,认定是因司马伷“率军出涂中”平吴而命名。
以上两种说法究竟那一种比较可信呢?笔者在主编新山志的工作中,为了把琅琊山命名的来源力争弄清楚,在学习参考近代各种有关琅琊山命名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和查阅了自唐宋以来的各种有关史志资料。现把这些历史资料全面作一介绍,并提出一些探讨的意见,同史志工作者、地理学者继续研究。
唐代房玄龄等撰编的《晋书》中,记载了司马伷和司马睿的简要历史和事迹。
司马伷是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叔父,原被封为东莞王,咸宁三年(277年)改封为琅邪王。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晋武帝大举伐吴,“遣镇东大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太康元年(280)二月,晋国的另两路平吴大军龙骧将军王濬、安东将军王浑直逼吴国的都城建邺(今南京市)时,吴主“孙皓穹蹙请降,送玺授于琅邪王伷”。该年三月,王濬的舟师到了建邺,孙皓才“面缚与榇”,向王濬投降。这段史实,在《晋书·武帝记》、《晋书·琅邪王伷传》和《三国志·吴志·嗣主传》中均有同样的记载,但“出涂中”指什么地方,各书均未注释。
司马睿是司马伷的孙子。太熙元年(290年)司马睿之父司马觐逝世,他世袭了琅邪王王位。永兴二年(305年)司马睿被封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永嘉元年(307年)七月,被封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今南京市)。当年九月,司马睿到达建邺。建兴元年(313年)秋八月,改建邺为建康。建兴四年(316年)十一月,晋愍帝司马邺向刘曜(后为前赵国皇帝)投降。次年三月,司马睿承制改元,称晋王于健康。太兴元年(318年)三月,晋愍帝遇弑的凶讯传至建康后,司马睿即皇帝位,称晋元帝。从此,史称东晋。从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到达建邺至永昌元年(322年)闰十一月逝世,司马睿在建康共住了十五年多的时间。关于司马睿有没有路过滁州,或“避难”、“尝住”滁州琅琊山,《晋书》没有记载。
除正史《晋书》外,在唐代文人写的其他地理志、碑刻、诗词、游记中,有关琅琊山名的来源,现在看到的还有四条资料。
在明万历版《滁阳志》、清康熙版《滁州志》和雍正四年御制的《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的艺文篇中,都辑存了唐代独孤及写的《琅琊溪述》。该文说:“按图经,晋元帝之居琅琊邸而为镇东也,尝游息是山,厥迹猶存。故长夫名溪曰琅琊”。长夫是唐大历六年(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的号。独孤及当时的职务,《新唐书》记他任过濠州(今安徽省定远县、凤阳县)和常州的刺史,《滁阳志》记他任过滁州刺史,是李幼卿的好友。独孤及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约在唐大历六年。
在《滁阳志》中还揖存了唐代诗人顾况(727—815年)写的一首诗《琅琊山》,诗的第一句为“东晋王家在此溪”,第三句为“碑沉字没昔人远”。顾况什么时候到过滁州,这首诗何时写的,志书中没有注明。据分析,约在李幼卿任滁州刺史的唐大历年代。
在清康熙版、光绪版的《滁州志》山川条中,还摘录了唐代崔祐甫(721—780年)写的宝应寺碑的一句话:“崔祐甫宝应寺碑亦云,东晋元帝初为琅琊嗣王逃难浮江未济徊翔之地也”。宝应寺是唐大历六年滁州刺史李幼卿与法琛法师所建,宝应寺碑也是那个时候写的。可惜该碑早已毁坏,碑记失传,至今找不到宝应寺碑的原文,无法进一步核实。
清康熙版《滁州志》山川条中还揖录了另一种说法:“唐李吉甫元和十道志云,晋武帝平吴,琅琊王伷出滁中,孙皓献玺即此地也”。清光绪版《滁州志》揖录这条资料时,只把“元和十道志”改为“元和郡县志”;“出滁中”改为“出涂中”。
《元和郡县志》原名《元和郡县图志》,是唐李吉甫编纂,于元和八年(813年)刻印的一部地理志。为了核实旧《滁州志》的记载是不是可信,我们查阅了现在看到的两种不同版本的《元和郡县图志》,一为清嘉庆岱南阁丛书本(影印);一为1983年6月由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本。两种版本均说明,《元和郡县图志》除两卷目录外,全书共有四十卷,宋代以后有六卷失传,只留存了三十四卷。其中,与滁州有关的“淮南道”是第二十四卷,原本早已失传,两种版本的“淮南道”都是后人补辑的。清嘉庆版本补记的“淮南道”第五页有一句:“汉全椒县地,晋琅琊王伷出涂中即此地(通鉴地理通释)”。中华书局新版中说明,该书的“淮南道”是清光绪七年缪荃孙补辑的。该书1076页有一句:“滁州,春秋时楚地,在汉为全椒县也(据宋《太平御览》卷百六十九),晋琅琊王伷出滁中即此地”。从这两种版本的《元和郡县图志》看,当时记载的“出涂中”或“出滁中”,都是指司马伷率军到过现在的全椒、滁州一带,并不是专门解释琅琊山因司马伷“率军出涂中”而命名。
宋代人写的有关琅琊山名来源的资料,我们查到了三条。
北宋文学家、至道元年(995年)任滁州知州的王禹偁,在他的著作《小畜集》中有一首题为“琅邪山”的诗,诗人自注说:“东晋元帝以琅邪王渡江尝驻此山,故溪山皆有琅邪之号,不知晋巳前何名也”。这条注解,清康熙版《滁州志》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在记载琅琊山时都全文作了揖录。
宋代乐史撰写的地理著作《太平寰宇记》(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刊本)卷之一百二十八“淮南道六”,记载滁州清流县条中有一句:“琅琊山在县西南十二里,其山始因东晋元帝为琅邪王避地此山,因名之”。
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年)王象之撰写的《舆地记胜》,是现在看到的最早对琅琊山地名来由两种说法进行探讨的一部地理著作。该书第四十二卷滁州“琅琊山”条目中,批驳了“晋元帝为琅邪王避地琅琊山”的说法,赞成因司马伷而命名的说法。原文是:“旧经云:晋元帝为琅邪王避地于此。按晋永兴二年八月,以琅邪王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永嘉元年七月己未(注:十一日),又以王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假节,镇建邺。其年九月戊申(注:初一日)至建邺,计其月日,不应避地此山。象之按元和郡县志:晋平吴,琅邪王伷出涂中,孙皓送玺,即此地也。”(注:抄录此文时,对照其他史书,“监徐州”,原文错写为“监滁州”,“出涂中”原文错写为“出滁州”,巳作改正。)
到了明代,文字记载琅琊山名由来的资料有好几篇。
明初史学家、主修《元史》的翰林院学士宋濂,于洪武八年(1373年)十一月陪同皇太子和诸王子去中都,途中经皇太子许可,邀四长史同游了琅琊山,撰写了《琅琊山游记》。该文说:“臣闻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晋元帝潜龙之地,帝尝封琅邪王,山因以名。
明代的滁州知州陈琏,根据南宋时龚维番撰写的《永阳郡志》残本,在永乐四年(1406年),撰写了一部《永阳志》。一百多年后,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当时的滁州知州林元伦邀请滁州人、进士胡松续编了一部《滁阳志》,都对琅琊山名的由来作过记载。这三部志书早已失传,但现在看到的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李之茂等纂修的《滁阳志》辑存了以上几部志书的记载。《滁阳志》卷之三“山川”一节165页的琅琊山条目的原文是:“琅琊山,在福山之阳十余里。旧志云:晋元帝为琅琊王避地于此,因是得名。或曰:晋武帝平吴,琅琊王伷出滁中,故山名琅琊也。胡志云:伷虽出滁中,未尝住此山,山何故因名?当元帝时,中国乱,元帝将渡江故避居此,后既称帝,江表人即其故号为山名耳。山上石壘遗迹尚存,此其尤可验者也。”这几部志书的撰修人,都对琅琊山名的由来,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证和探讨,值得我们后人重视。
在清代的地理著作和方志中,除康熙版、光绪版《滁州志》,对琅琊山名的由来采用了两说并存的记载方法外,还查到了两种不同态度的记载。
一种是清初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本)的记载。该书第二十九卷1314页“琅琊山”条写道:“州南十里。晋伐吴,命琅邪王伷出涂中时尝住此,因名。”
另一种是清代文人缪荃孙的辑录。缪荃孙在查阅了古代的历史地理著作后,于光绪七年(1881年)为唐代的《元和郡县志》补辑了三卷逸文。据初步查对,他在补辑“淮南道”卷中有关滁州的沿革和山川的逸文共九条,其中有七条辑自南宋王象之写的《舆地纪胜》,但《舆地纪胜》中关于琅琊山名由来的说法,缪荃孙没有辑录,却采用了宋代王应麟撰写的《通 地理通释》的说法,指出“晋琅邪王伷出涂中,即此地”,是指的滁州,不是专指琅琊山。
地理通释》的说法,指出“晋琅邪王伷出涂中,即此地”,是指的滁州,不是专指琅琊山。
以上是我们现已查到的一些原始资料。由于许多古籍多年失传,藏本稀少,这次修志的时间和人力有限,有些历史资料至今尚未查到,笔者和参加新编《琅琊山志》编纂委员会的同志们,作了几次讨论,就已征集到的资料,对探讨琅琊山名的来源,提出几点意见。
我们认为,在探讨山名由来时,既要重视正史和地理名著的记载,也不能忽视地方志及其他历史文献和文物的记载。有的同志认为,正史和地理名著的记载,比方志、碑文、诗词、游记的记载更准确,这就一般情况看,是合乎实际的。但就琅琊山这个具体的山来说,历史上到过滁州的文人和在滁州任职的官员不乏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经过实地考察后撰写的方志、碑文、诗词、游记,和正史、地理名著一样,也有一定的根据,不要轻易否定。我们在修志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发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历代撰编的正史、地理总志和当地方志中,都有一些漏记的史实,都有一些“以讹传讹”的错误记载。我们当代的史学、方志以及地理学工作者,应全面搜集资料,兼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多方考证核实,尽力把一些不准确的历史记载搞准,以供后人参考。
就司马伷和司马睿是不是到过琅琊山这件历史事实来说,司马伷在平吴时“率军出涂中”、孙皓向司马伷“送玺请降”,《晋书》和《三国志》中均有记载。尽管后人的地理著作和方志中,有人指出“涂中”是泛指现在安徽省的滁州、全椒,江苏的六合(古代叫“堂邑”)一带,不是专指琅琊山,但琅琊山只离滁州城西南十里,司马伷率军到过滁州就包括了琅琊山,因而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那么,司马睿是不是到过滁州琅琊山呢?虽然《晋书》上没有记载,但同编《晋书》唐贞观年代较接近的唐代人李幼卿、独孤及、顾况以及宋初的王禹偁等人,根据琅琊山的碑刻、遗迹对照史书的记载,认为琅琊山是因“晋元帝避地于此”而得名,也有根据。有些地理学者、史学者,在探讨琅琊山名来源时,根据正史的记载,从司马睿率军由下邳转移到建邺的时间只有五十天,按当时的地理形势走水路比走陆路近,来进行推理,认为司马睿不可能路过滁州,也不会“避难”于琅琊山。这种探讨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只是一种推理,现在还找不到充分的根据来证明李幼卿、独孤及、王禹偁等人的记载不可信。
我们还认为,要弄清琅琊山名的由来,除了琅邪王司马伷、司马睿到过这一带这个主要因素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和形势变化,需要综合起来进行研究。
不少历史地理著作都记载,早在秦代,现山东省东南部胶南县的南境,有一座琅邪山。《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南登琅邪,作琅邪台,就在琅邪山下的滨海之地。秦代在这一带设了琅邪郡,后又增置了琅邪县,东汉改置琅邪国。到了西晋增置了“东莞郡”,琅邪王的封地已从山东南部的滨海地区转移到临沂地区,即现在的苍山、费县、蒙阴、沂南、临沂等县。
至于滁州的琅琊山,在东晋以前不知叫什么名字,也没有什么名气。据传东晋时山上修了玉皇殿,当时是不是巳开始叫琅琊山,现在查不到可信的根据。现在有文字记载的,是距离东晋三百多年后的唐大历六年(771年),当时的滁州刺史李幼卿与法琛法师在山上修建宝应寺,开凿泉水,才根据多年来流传的晋元帝“尝游息是山”的说法,将此山此溪命名为“琅琊山”、“琅琊溪”。
山东省有一座琅邪山,西晋几位琅邪王的封地都在山东,怎么会到了东晋和唐代要把滁州城西南的一座小山也重名为琅琊山呢?这同当时的形势变化、司马伷和司马睿两位琅邪王中谁在滁州一带的影响大,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来命名的,都有密切的关系。
试把司马伷和司马睿在滁州一带的影响作一比较:
司马伷只是一位亲王。他从咸宁三年被晋武帝由东莞王改封为琅邪王后,到咸宁五年率军伐吴,任琅邪王才两年的时间。西晋平吴的战争前后只有五个月(咸宁五年十一月到太康元年三月),除去来回行军,司马伷在滁州一带驻军的时间不过三、四个月。司马睿在到达滁州和建邺以前,已经世袭了27年琅邪王(从太熙元年到建兴四年),后来又当上了皇帝。他不仅到过滁州琅琊山一带,而且在与滁州一江之隔的建康(今南京市)住了十五年多的时间。
两相比较,司马睿在滁州一带的影响要比司马伷大。因为皇帝在任琅邪王时到过这里而命名琅琊山,这是一般后人所能接受的,也是历史上的习惯做法。
更为重要的情况是,司马伷“率军出涂中”时,才建立的西晋王朝比较巩固,琅邪王的封地在山东,山东已有琅邪山,用不着因司马伷到过滁州,就把滁州的一座小山命名琅琊山。而司马睿到达滁州、建康时的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西晋王朝因八王之乱,连年战祸已逐渐衰亡,到了建兴四年(316年),原在山东琅邪国的封地已被外臣占领。司马睿自封晋王,不久又当了晋元帝后,取消了琅邪国的封号,原在山东琅邪国封土上的大批臣民,因不堪外人的压迫,纷纷向南迁移。据《晋书·元帝纪》的记载,大兴三年(320年)秋七月,元帝下诏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临君琅邪四十余年,惠泽加于百姓,遗爱结于人情。联应天符,创基江表,兆蔗它心,襁负子来。琅邪国人在此者近有千户,今立为怀德县,统丹杨郡……。”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有些地理历史著作指出,东晋时的怀德县约在今江苏省江浦县的西境,丹杨郡后改为丹杨尹,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据《晋书》记载,晋元帝不只是下诏设置了怀德县,安置南迁的原琅邪国臣民,以后又“侨置琅邪郡于江南,分江乘县(今江苏省句容县北)地为实土”。在东晋王朝(公元317到420年)的一百多年内,连晋元帝司马睿在内共有十一位皇帝,每位皇帝即位后,都封了其亲属中的一人为琅邪王,当时琅邪王的封地,都在江南。那时,江南的一些地名、山名都有了改动。
还有一条值得重视的历史事实,在东晋王朝的十一位皇帝中,先被封为琅邪王后当皇帝的,除元帝司马睿以外,还有五人。他们是:康帝司马岳,哀帝司马丕,废帝司马奕,简帝司马昱,恭帝司马德文。有六位皇帝在即位前都是琅邪王,琅邪王的名位在整个东晋时代,影响很大。
根据以上情况,特别是原山东籍“琅邪国”的大批臣民南迁,晋元帝将江南的几个县改封为琅邪郡以后,琅邪王的称号,在大江南北(包括滁州地区)广大臣民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时,才有可能按照琅邪王的称号,把属于淮南道的滁州的一座小山重名为“琅邪山”。关于这一点,前面引证的明万历《滁阳志》中记载的一段话,值得重视:“山何故因名,当元帝时,中国乱,元帝将渡江故避此,后既称帝,江表人即其故号为山名耳”。这里所说的“江表人”,是泛指今南京、江浦一带的本地人和山东南迁的“侨民”。虽然对晋元帝在渡江前是不是“避此”至今史学界有所争论,但滁州琅琊山这个名字,是在东晋时“江表人”首先口头命名的,这是一件历史事实。这正是唐代的滁州刺史李幼卿命名“琅琊山”、“琅琊溪”的根据。
纵观以上历史资料,我们总的看法是:滁州琅琊山名的由来,主要是因司马睿而命名,证据比较充分。但不能排斥或否定因司马伷而命名的说法,因为司马伷确实到过滁州,在平吴战争因吴主孙皓向他“送玺请降”立了大功,这也是历史事实。对历史上的这样一件大事,后代的地理著作和当地方志的撰写人会予以重视,以此来解释琅琊山名的由来。因此,我们认为,琅琊山名由来的两种说法,都是历史事实,不是“以讹传讹”的错误记载。从当时的整体形势推理,因司马睿而命名的根据更多,是主要的来源。作为志书,对由司马伷而命名的资料,也应全部记载,以让后代对这段历史有一全面的客观的了解。
最后,还有一个“琅邪王”和“琅琊山”的书写标准化的问题。根据史书的文字记载,自秦。汉至于晋代,无论地名、郡名、国名都写“琅邪”。唐代人编写的“晋书”,仍写为“琅邪王”、“琅邪郡”。“邪”在地名上使用时念yè(耶),不念邪恶的“邪”,也不念“牙”。滁州的琅琊山命名后,宋乐史编的《太平寰宇记》仍写“琅邪王”、“琅邪山”。宋代书法家苏轼写的题字和碑刻中,根据同音字写为“琅耶山”,直至清代和当代,不少地理著作仍写“琅邪王”、“琅邪山”。但至唐宋以来的大多数志书、游记、诗词,可能因口音不同,或是相互抄录,逐渐把“琅邪山”改写为“琅琊山”(琊字念“牙”),并用繁体字写为“ 玡山”、有的甚至把“琅邪王”,也改写为“琅琊王”,出现了一名多写的混乱情况。根据新编志书地名写法要规范统一的要求,在编纂新的《琅琊山志》时,我们根据滁州市地名办公室的规定,按照多年来的俗称,统一写为“琅琊山”,不写也不叫“琅邪山”、“琅耶山”,并按照国家文字机构颁布的简化字书写。至于“琅邪王”,应该照历史称呼书写,不能错写为“琅琊王”。这部新山志和这篇专文,只有在引证历史文献时,为保持原作的真实,原文怎样写就怎样写;由编纂者写的概述、大事记以及专文,则统一写为“琅邪王”、“琅琊山”,以避免一名多写的混乱现象。目前,全国各地还有几座同名山:河北省有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五壮士英勇抗敌的狼牙山;山东省有秦始皇到过的琅邪山;江苏南部句容县也有同名山。为了让全国的读者不棍淆地理概念,我们提议,在各地同名山的前面,加上所属省名,我们这座琅琊山电皤称叫“安徽省滁州琅琊山”。
玡山”、有的甚至把“琅邪王”,也改写为“琅琊王”,出现了一名多写的混乱情况。根据新编志书地名写法要规范统一的要求,在编纂新的《琅琊山志》时,我们根据滁州市地名办公室的规定,按照多年来的俗称,统一写为“琅琊山”,不写也不叫“琅邪山”、“琅耶山”,并按照国家文字机构颁布的简化字书写。至于“琅邪王”,应该照历史称呼书写,不能错写为“琅琊王”。这部新山志和这篇专文,只有在引证历史文献时,为保持原作的真实,原文怎样写就怎样写;由编纂者写的概述、大事记以及专文,则统一写为“琅邪王”、“琅琊山”,以避免一名多写的混乱现象。目前,全国各地还有几座同名山:河北省有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五壮士英勇抗敌的狼牙山;山东省有秦始皇到过的琅邪山;江苏南部句容县也有同名山。为了让全国的读者不棍淆地理概念,我们提议,在各地同名山的前面,加上所属省名,我们这座琅琊山电皤称叫“安徽省滁州琅琊山”。
一九八八年五月
(韩枫,原任滁县地区编史修志办公室主任兼中共滁县地委党史办公室主任,现已离休。)
环滁皆山
江流
一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开头第一句就说:“环滁皆山也。”各种文集中对这一句话的注释,大都只说“环:环绕。滁:即滁州。”那么“皆山”又指哪些山?共有多少座山?却从未见有人具体注释过。据《朱子语类》第一三九卷称:“欧公文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原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可惜,我们今天连欧阳修原稿中概括叙述的“凡数十字”都已见不到,难怪一般注释家只好略而不谈了。
单说“环滁”的“滁”字,小而言之,仅指原来的滁县,即今日的滁州市,那么在它的东西南北四面,共有大小山头约七十座(详见附注)。如果大而言之,指宋代的滁州州治范围而言,它包括今天三个县以上的地区,那么其山峰的总数,就不是几十座,而是几百座了。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了王俊坤的《“环滁皆山”小议》一文,编者在第一版把它列入“今日本报要目”。并赫然宣告说:“欧阳修观察有误,谬写‘环滁皆山,——请看第二版《‘环滁皆山’小议》。”·翻到第二版,《‘环滁皆山’小议》一开头就武断地说:
“到过滁州的人都知道,滁州除了城西和西北方向有山以外,东和东北方向皆不见山。欧阳公所谓‘环滁皆山’与事实不合。将一‘滁’的范围从州治所在地的滁城,扩大到整个滁州(包括现今滁县、来安、全椒三县),‘环滁皆山’还是得不到坐实。……所以‘环滁皆山’的描述有观察失真、概括失当之谬……使人颇感不解的是,自《醉翁亭记》间世九百余年来,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却无人敢对其首句有所誉议”。接下去,还发了一大通议论,说什么“其一,读书应戴自己的眼镜”,其二,不必为名家、名篇讳言……应该旗帜鲜明地指出其谬误”云云,这里就无须多引了。
这位作者是否曾经乘车经过滁州车站,我自然无从断定。但可绝对肯定地说,他不仅没有到滁城周围实地看一看过,甚至连《滁州志》、《滁县乡土志》、《滁州市地名录》这一类最起码的现成资料,也根本没沾过边,却公然就“敢”“戴自己的眼镜”大发“訾议”,不仅“旗帜鲜明地”诬陷欧阳修“谬误”和“失真”,而且把“九百余年来”的读者一概骂倒。如此拿腔做调,信口雌黄,俨然“唯我独革”的文风,跟我们在“文革中司空见惯的那些所谓“革命大字报”的语气,何其相似乃尔!然而今天总不会再出现一个秦始皇,能挥起那根神话中的“赶山鞭”,把那些客观存在的山头,纷纷赶下海去吧?
二
博学多才的欧阳修,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单就舆地知识来说,从书本知识到感性知识,他都颇为渊博。他早年参加进士考试一举成名,考试题就是《司空掌舆地之图赋》,曾被主考官晏殊称赞说:“今一场举子,唯他一个人识题!”他当滁州太守后,也并非仅是常到“西南诸峰”之间去留连(他到滁州是被贬谪下来的,他自称“醉翁”,是佯狂诗酒,以掩权奸之耳目),实际上他是经常深入民间。滁州城东五里处有一菱溪,他就曾多次前去观察那里的石头,甚至引起群众的怀疑。他曾在诗中记述此事说:“溪边老翁生长见,凝我来视何殷勤。”这样的一位欧阳修,如果真的是城南、城东和东北方向“皆不见山”,他怎么诌出“环滁皆山”这一名句来呢?笑话!
地方建制沿革,常常是有变迁的。以宋代的滁州而言,其实也不仅是现在的滁州市(即原滁县)、全椒、来安三县的范围,它还包括现在嘉山县的一部分。嘉山是一九三二年新设的县,它的一部分就是由滁县、来安划出去的,例如原属滁县的张八岭,现在则属嘉山。滁州始置于隋,唐天宝初年改州为郡,以当时“州北三里”有永阳岭而命名为永阳郡。而这个永阳岭,如今则属来安县,在来安县城东偏北,距滁州市则有三十多华里。可见唐代和宋代之间,连州治的首府所在地也并不相同。
三
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其实不仅地方建制常有变迁,就连种种自然形态,也在不断地变异。一般地说,象山脉的情况,几百年间该不会有多少变化吧?其实不然。我们考核一下旧的《滁州志》,它初编于清康熙年间,最后重编于光绪年间,先后相距不过二百年左右。但在光绪年间重新编修时,就发现旧志中原有的十五座小山头,已经查访不着了!
滁州一带部分属山区,但多数则属丘陵地带。即以本文附注中所列的滁州市现有的七十座山为例,其中最高峰是北将军,海拔也还不到四百米;而象滁东赫赫有名的古迹皇道山,不过海拔数十米而已。这些低矮的小山和丘陵,是古淮阳山脉东翼的余脉,如果在我国山脉系统中论资排辈的话,它们称得上是老祖宗一辈。(至于目前世界最高峰所在的喜马拉雅山脉,从造山运动史的角度来衡量,它在山的庞大氏族中,只不过是少年儿童罢了。)但远古时代的大山,经过漫长历史世纪的不断侵蚀摧残,高度逐渐降低、有的甚至已成丘陵,也还有比丘陵被侵蚀得更厉害的准平原,实际上已经看不出“山”的任何面目来了。一九五六年我曾到嘉山县的平湖农庄访问(那里原属古滁州的范围之内),当时经勘察,那里土地中所含的砂石量,平均达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五点五。用拖拉机犁地,犁尖与翻土板的损耗率高得惊人。在夜间,拖拉机从地里开过时,遍地火星飞溅,那可以说正是“山魂”在显形。
在社会发展中,人口的变化也值得注意。翻开《宋史》来看,欧阳修时代的滁州人口,跟今天同一范围内的人口相比,当时的人口不过仅及今日人口的百分之六左右,地广而人稀。今日的低矮山包和丘陵,大都已化为农田和村落,而在昔日,则是树木荫森,虎狼出没,行为裹足,视为畏途,是道道地地的荒山和野岭。(明清时代一些著名的记叙文,对滁城附近老虎出没的具体形象和气氛都有记载。)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体味欧阳修所写的“环滁皆山”,才会更加形象逼真。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五日完稿
〔附注〕滁州市周围的山峦细列如下:
北有白米山、锅底山、牛牧岭、魏山岗、砂子岭、关山、棺材山。
东北有乌龙山、独山、大桂山、小桂山。
东有皇道山、姚大山、团山、林江墩。
东南有毛山。
南有大龙头、毛谷山、赵家大山、狐山、龙尾山、庙山。
西南有琅琊山、大丰山、鸡冠石、花山、绿豆山、菱角山、扁担山、庙山、狼头山、指马山、黄大山、宝塔山、江家山、妈蚁山、三百丈、凤凰山、杨梅山、瞌睡岭、炮楼山、南将军、老虎山、天尖山、尖山里、黑狼庙、滑鼻山、雁塘山、五尖山。
西有大尖山、团山、烟墩山、小红山、长山、皇甫寺(山)、相山、五斗山、磨刀石山、大山包、乌龟山、小磨盘山、小尖山之一、小尖山之二、宝塔山、烟龙包、狮子庙、张山尖、皇甫山、北将军、将军庙。
(江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安微省分会副主席。)
《醉翁亭记》碑文的几处考订
余炳华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我国文坛上著名的一篇散文。其韵味浓厚,诗情画意无穷,把琅琊山的风光描绘得绚丽多彩,引人入胜,实为古今中外人们喜读的好文章。由于这篇名著的问世,滁州琅琊山逐渐被历史名人所关注,招引不少名人来游,题咏琅琊山景色的文章,由古至今如泉涌而出。
多年来,国内不少文史工作者,常有著述描写醉翁亭,并附录《醉翁亭记》全文,或摘录其文名句,或是介绍它的意境和写作方法。但是,有些作者由于未能亲临其境,目睹其碑,以至把这篇名著的原文抄录错误。由于同样原因,有些出版部门的编者,难以识别错处,将抄录有错的《醉翁亭记》正式编入书刊,广泛流传社会,使读者曲解此文的意境,降低此文的历史价值。翻为滁州的文史工作者,虽未亲眼见过欧阳修自书的《醉翁亭记》碑刻,而对苏轼所书的《醉翁亭记》碑刻却随时可以拜读(苏轼书写的碑刻现仍在滁州市醉翁亭的宝宋斋内)。由于沧桑变迁,此碑已经剥脱不全。多年来,我搜集了一些版本的《醉翁亭记》碑帖,按照原碑一一作了校订,发现中华书局1982年6月出版的《古文观止》中《醉翁亭记》错字较多,丢字、错字和错句竟达十三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的《欧阳修》一书,原文照录的《醉翁亭记》,有六个错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的《欧阳修》所附录的此记,也有六个错字。除此而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的《醉翁亭记》帖本,可以算是目前最好的版本了。但是,其中的序和抄本也有三处差错。
对于《醉翁亭记》这篇文章,我们应该视作民族文化遗产,要保存其原貌,不应在引用时改变其原文,以免贻误我们对欧阳修诗文的研究。
对于原文中“让泉”的“让”字,不应误用“酿”字;“水清而石出”的“清”字,不应误用“落”字;“莫而归”的“莫”字,在此文中虽然可以作为“暮”字用,如果作为原文引用,则应该用“莫”字。为了方便读者,可以在“莫”字后面写个“(暮)”,以作注释。“负者歌于途”的“途”字,不应误用“涂”和“塗”字。“太守燕也”、“燕酣之乐”两处的“燕”字,在这里就是“宴”字的代用字,也用上述方法处理。“坐起而喧哗者”的“坐起”二字,原碑实为“起坐”。原碑跋文中有“字画浅褊”,而光绪二十三年版本的《滁州志》却误为“字画褊浅”。对以上诸问题,我们应该正确订正,而出版部门,更需要认真以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碑帖进行校核。这样,才能保证这篇名著原原本本地流传于世。
(余炳华,现任滁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韩枫
琅琊山名的由来,自唐宋至今,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因西晋琅邪王司马伷而定名;二是因先任琅邪王后来当上了东晋元帝的司马睿而定名。
对这两种说法,清代、民国和当代的史志学者、地理学者,在编纂“琅琊山”条目时,采用了不同的记载方法。有的采用了两说並存;有的只记因晋元帝司马睿到此而定名这一种说法,有的认为司马睿到过琅琊山的说法不可信,认定是因司马伷“率军出涂中”平吴而命名。
以上两种说法究竟那一种比较可信呢?笔者在主编新山志的工作中,为了把琅琊山命名的来源力争弄清楚,在学习参考近代各种有关琅琊山命名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和查阅了自唐宋以来的各种有关史志资料。现把这些历史资料全面作一介绍,并提出一些探讨的意见,同史志工作者、地理学者继续研究。
唐代房玄龄等撰编的《晋书》中,记载了司马伷和司马睿的简要历史和事迹。
司马伷是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叔父,原被封为东莞王,咸宁三年(277年)改封为琅邪王。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晋武帝大举伐吴,“遣镇东大将军琅邪王伷出涂中”。太康元年(280)二月,晋国的另两路平吴大军龙骧将军王濬、安东将军王浑直逼吴国的都城建邺(今南京市)时,吴主“孙皓穹蹙请降,送玺授于琅邪王伷”。该年三月,王濬的舟师到了建邺,孙皓才“面缚与榇”,向王濬投降。这段史实,在《晋书·武帝记》、《晋书·琅邪王伷传》和《三国志·吴志·嗣主传》中均有同样的记载,但“出涂中”指什么地方,各书均未注释。
司马睿是司马伷的孙子。太熙元年(290年)司马睿之父司马觐逝世,他世袭了琅邪王王位。永兴二年(305年)司马睿被封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永嘉元年(307年)七月,被封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今南京市)。当年九月,司马睿到达建邺。建兴元年(313年)秋八月,改建邺为建康。建兴四年(316年)十一月,晋愍帝司马邺向刘曜(后为前赵国皇帝)投降。次年三月,司马睿承制改元,称晋王于健康。太兴元年(318年)三月,晋愍帝遇弑的凶讯传至建康后,司马睿即皇帝位,称晋元帝。从此,史称东晋。从永嘉元年(307年)九月到达建邺至永昌元年(322年)闰十一月逝世,司马睿在建康共住了十五年多的时间。关于司马睿有没有路过滁州,或“避难”、“尝住”滁州琅琊山,《晋书》没有记载。
除正史《晋书》外,在唐代文人写的其他地理志、碑刻、诗词、游记中,有关琅琊山名的来源,现在看到的还有四条资料。
在明万历版《滁阳志》、清康熙版《滁州志》和雍正四年御制的《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的艺文篇中,都辑存了唐代独孤及写的《琅琊溪述》。该文说:“按图经,晋元帝之居琅琊邸而为镇东也,尝游息是山,厥迹猶存。故长夫名溪曰琅琊”。长夫是唐大历六年(771年)滁州刺史李幼卿的号。独孤及当时的职务,《新唐书》记他任过濠州(今安徽省定远县、凤阳县)和常州的刺史,《滁阳志》记他任过滁州刺史,是李幼卿的好友。独孤及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约在唐大历六年。
在《滁阳志》中还揖存了唐代诗人顾况(727—815年)写的一首诗《琅琊山》,诗的第一句为“东晋王家在此溪”,第三句为“碑沉字没昔人远”。顾况什么时候到过滁州,这首诗何时写的,志书中没有注明。据分析,约在李幼卿任滁州刺史的唐大历年代。
在清康熙版、光绪版的《滁州志》山川条中,还摘录了唐代崔祐甫(721—780年)写的宝应寺碑的一句话:“崔祐甫宝应寺碑亦云,东晋元帝初为琅琊嗣王逃难浮江未济徊翔之地也”。宝应寺是唐大历六年滁州刺史李幼卿与法琛法师所建,宝应寺碑也是那个时候写的。可惜该碑早已毁坏,碑记失传,至今找不到宝应寺碑的原文,无法进一步核实。
清康熙版《滁州志》山川条中还揖录了另一种说法:“唐李吉甫元和十道志云,晋武帝平吴,琅琊王伷出滁中,孙皓献玺即此地也”。清光绪版《滁州志》揖录这条资料时,只把“元和十道志”改为“元和郡县志”;“出滁中”改为“出涂中”。
《元和郡县志》原名《元和郡县图志》,是唐李吉甫编纂,于元和八年(813年)刻印的一部地理志。为了核实旧《滁州志》的记载是不是可信,我们查阅了现在看到的两种不同版本的《元和郡县图志》,一为清嘉庆岱南阁丛书本(影印);一为1983年6月由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本。两种版本均说明,《元和郡县图志》除两卷目录外,全书共有四十卷,宋代以后有六卷失传,只留存了三十四卷。其中,与滁州有关的“淮南道”是第二十四卷,原本早已失传,两种版本的“淮南道”都是后人补辑的。清嘉庆版本补记的“淮南道”第五页有一句:“汉全椒县地,晋琅琊王伷出涂中即此地(通鉴地理通释)”。中华书局新版中说明,该书的“淮南道”是清光绪七年缪荃孙补辑的。该书1076页有一句:“滁州,春秋时楚地,在汉为全椒县也(据宋《太平御览》卷百六十九),晋琅琊王伷出滁中即此地”。从这两种版本的《元和郡县图志》看,当时记载的“出涂中”或“出滁中”,都是指司马伷率军到过现在的全椒、滁州一带,并不是专门解释琅琊山因司马伷“率军出涂中”而命名。
宋代人写的有关琅琊山名来源的资料,我们查到了三条。
北宋文学家、至道元年(995年)任滁州知州的王禹偁,在他的著作《小畜集》中有一首题为“琅邪山”的诗,诗人自注说:“东晋元帝以琅邪王渡江尝驻此山,故溪山皆有琅邪之号,不知晋巳前何名也”。这条注解,清康熙版《滁州志》和《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在记载琅琊山时都全文作了揖录。
宋代乐史撰写的地理著作《太平寰宇记》(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刊本)卷之一百二十八“淮南道六”,记载滁州清流县条中有一句:“琅琊山在县西南十二里,其山始因东晋元帝为琅邪王避地此山,因名之”。
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年)王象之撰写的《舆地记胜》,是现在看到的最早对琅琊山地名来由两种说法进行探讨的一部地理著作。该书第四十二卷滁州“琅琊山”条目中,批驳了“晋元帝为琅邪王避地琅琊山”的说法,赞成因司马伷而命名的说法。原文是:“旧经云:晋元帝为琅邪王避地于此。按晋永兴二年八月,以琅邪王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永嘉元年七月己未(注:十一日),又以王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假节,镇建邺。其年九月戊申(注:初一日)至建邺,计其月日,不应避地此山。象之按元和郡县志:晋平吴,琅邪王伷出涂中,孙皓送玺,即此地也。”(注:抄录此文时,对照其他史书,“监徐州”,原文错写为“监滁州”,“出涂中”原文错写为“出滁州”,巳作改正。)
到了明代,文字记载琅琊山名由来的资料有好几篇。
明初史学家、主修《元史》的翰林院学士宋濂,于洪武八年(1373年)十一月陪同皇太子和诸王子去中都,途中经皇太子许可,邀四长史同游了琅琊山,撰写了《琅琊山游记》。该文说:“臣闻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晋元帝潜龙之地,帝尝封琅邪王,山因以名。
明代的滁州知州陈琏,根据南宋时龚维番撰写的《永阳郡志》残本,在永乐四年(1406年),撰写了一部《永阳志》。一百多年后,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当时的滁州知州林元伦邀请滁州人、进士胡松续编了一部《滁阳志》,都对琅琊山名的由来作过记载。这三部志书早已失传,但现在看到的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李之茂等纂修的《滁阳志》辑存了以上几部志书的记载。《滁阳志》卷之三“山川”一节165页的琅琊山条目的原文是:“琅琊山,在福山之阳十余里。旧志云:晋元帝为琅琊王避地于此,因是得名。或曰:晋武帝平吴,琅琊王伷出滁中,故山名琅琊也。胡志云:伷虽出滁中,未尝住此山,山何故因名?当元帝时,中国乱,元帝将渡江故避居此,后既称帝,江表人即其故号为山名耳。山上石壘遗迹尚存,此其尤可验者也。”这几部志书的撰修人,都对琅琊山名的由来,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证和探讨,值得我们后人重视。
在清代的地理著作和方志中,除康熙版、光绪版《滁州志》,对琅琊山名的由来采用了两说并存的记载方法外,还查到了两种不同态度的记载。
一种是清初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本)的记载。该书第二十九卷1314页“琅琊山”条写道:“州南十里。晋伐吴,命琅邪王伷出涂中时尝住此,因名。”
另一种是清代文人缪荃孙的辑录。缪荃孙在查阅了古代的历史地理著作后,于光绪七年(1881年)为唐代的《元和郡县志》补辑了三卷逸文。据初步查对,他在补辑“淮南道”卷中有关滁州的沿革和山川的逸文共九条,其中有七条辑自南宋王象之写的《舆地纪胜》,但《舆地纪胜》中关于琅琊山名由来的说法,缪荃孙没有辑录,却采用了宋代王应麟撰写的《通
 地理通释》的说法,指出“晋琅邪王伷出涂中,即此地”,是指的滁州,不是专指琅琊山。
地理通释》的说法,指出“晋琅邪王伷出涂中,即此地”,是指的滁州,不是专指琅琊山。以上是我们现已查到的一些原始资料。由于许多古籍多年失传,藏本稀少,这次修志的时间和人力有限,有些历史资料至今尚未查到,笔者和参加新编《琅琊山志》编纂委员会的同志们,作了几次讨论,就已征集到的资料,对探讨琅琊山名的来源,提出几点意见。
我们认为,在探讨山名由来时,既要重视正史和地理名著的记载,也不能忽视地方志及其他历史文献和文物的记载。有的同志认为,正史和地理名著的记载,比方志、碑文、诗词、游记的记载更准确,这就一般情况看,是合乎实际的。但就琅琊山这个具体的山来说,历史上到过滁州的文人和在滁州任职的官员不乏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经过实地考察后撰写的方志、碑文、诗词、游记,和正史、地理名著一样,也有一定的根据,不要轻易否定。我们在修志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发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历代撰编的正史、地理总志和当地方志中,都有一些漏记的史实,都有一些“以讹传讹”的错误记载。我们当代的史学、方志以及地理学工作者,应全面搜集资料,兼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多方考证核实,尽力把一些不准确的历史记载搞准,以供后人参考。
就司马伷和司马睿是不是到过琅琊山这件历史事实来说,司马伷在平吴时“率军出涂中”、孙皓向司马伷“送玺请降”,《晋书》和《三国志》中均有记载。尽管后人的地理著作和方志中,有人指出“涂中”是泛指现在安徽省的滁州、全椒,江苏的六合(古代叫“堂邑”)一带,不是专指琅琊山,但琅琊山只离滁州城西南十里,司马伷率军到过滁州就包括了琅琊山,因而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那么,司马睿是不是到过滁州琅琊山呢?虽然《晋书》上没有记载,但同编《晋书》唐贞观年代较接近的唐代人李幼卿、独孤及、顾况以及宋初的王禹偁等人,根据琅琊山的碑刻、遗迹对照史书的记载,认为琅琊山是因“晋元帝避地于此”而得名,也有根据。有些地理学者、史学者,在探讨琅琊山名来源时,根据正史的记载,从司马睿率军由下邳转移到建邺的时间只有五十天,按当时的地理形势走水路比走陆路近,来进行推理,认为司马睿不可能路过滁州,也不会“避难”于琅琊山。这种探讨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只是一种推理,现在还找不到充分的根据来证明李幼卿、独孤及、王禹偁等人的记载不可信。
我们还认为,要弄清琅琊山名的由来,除了琅邪王司马伷、司马睿到过这一带这个主要因素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和形势变化,需要综合起来进行研究。
不少历史地理著作都记载,早在秦代,现山东省东南部胶南县的南境,有一座琅邪山。《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南登琅邪,作琅邪台,就在琅邪山下的滨海之地。秦代在这一带设了琅邪郡,后又增置了琅邪县,东汉改置琅邪国。到了西晋增置了“东莞郡”,琅邪王的封地已从山东南部的滨海地区转移到临沂地区,即现在的苍山、费县、蒙阴、沂南、临沂等县。
至于滁州的琅琊山,在东晋以前不知叫什么名字,也没有什么名气。据传东晋时山上修了玉皇殿,当时是不是巳开始叫琅琊山,现在查不到可信的根据。现在有文字记载的,是距离东晋三百多年后的唐大历六年(771年),当时的滁州刺史李幼卿与法琛法师在山上修建宝应寺,开凿泉水,才根据多年来流传的晋元帝“尝游息是山”的说法,将此山此溪命名为“琅琊山”、“琅琊溪”。
山东省有一座琅邪山,西晋几位琅邪王的封地都在山东,怎么会到了东晋和唐代要把滁州城西南的一座小山也重名为琅琊山呢?这同当时的形势变化、司马伷和司马睿两位琅邪王中谁在滁州一带的影响大,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来命名的,都有密切的关系。
试把司马伷和司马睿在滁州一带的影响作一比较:
司马伷只是一位亲王。他从咸宁三年被晋武帝由东莞王改封为琅邪王后,到咸宁五年率军伐吴,任琅邪王才两年的时间。西晋平吴的战争前后只有五个月(咸宁五年十一月到太康元年三月),除去来回行军,司马伷在滁州一带驻军的时间不过三、四个月。司马睿在到达滁州和建邺以前,已经世袭了27年琅邪王(从太熙元年到建兴四年),后来又当上了皇帝。他不仅到过滁州琅琊山一带,而且在与滁州一江之隔的建康(今南京市)住了十五年多的时间。
两相比较,司马睿在滁州一带的影响要比司马伷大。因为皇帝在任琅邪王时到过这里而命名琅琊山,这是一般后人所能接受的,也是历史上的习惯做法。
更为重要的情况是,司马伷“率军出涂中”时,才建立的西晋王朝比较巩固,琅邪王的封地在山东,山东已有琅邪山,用不着因司马伷到过滁州,就把滁州的一座小山命名琅琊山。而司马睿到达滁州、建康时的情况,已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西晋王朝因八王之乱,连年战祸已逐渐衰亡,到了建兴四年(316年),原在山东琅邪国的封地已被外臣占领。司马睿自封晋王,不久又当了晋元帝后,取消了琅邪国的封号,原在山东琅邪国封土上的大批臣民,因不堪外人的压迫,纷纷向南迁移。据《晋书·元帝纪》的记载,大兴三年(320年)秋七月,元帝下诏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临君琅邪四十余年,惠泽加于百姓,遗爱结于人情。联应天符,创基江表,兆蔗它心,襁负子来。琅邪国人在此者近有千户,今立为怀德县,统丹杨郡……。”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有些地理历史著作指出,东晋时的怀德县约在今江苏省江浦县的西境,丹杨郡后改为丹杨尹,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据《晋书》记载,晋元帝不只是下诏设置了怀德县,安置南迁的原琅邪国臣民,以后又“侨置琅邪郡于江南,分江乘县(今江苏省句容县北)地为实土”。在东晋王朝(公元317到420年)的一百多年内,连晋元帝司马睿在内共有十一位皇帝,每位皇帝即位后,都封了其亲属中的一人为琅邪王,当时琅邪王的封地,都在江南。那时,江南的一些地名、山名都有了改动。
还有一条值得重视的历史事实,在东晋王朝的十一位皇帝中,先被封为琅邪王后当皇帝的,除元帝司马睿以外,还有五人。他们是:康帝司马岳,哀帝司马丕,废帝司马奕,简帝司马昱,恭帝司马德文。有六位皇帝在即位前都是琅邪王,琅邪王的名位在整个东晋时代,影响很大。
根据以上情况,特别是原山东籍“琅邪国”的大批臣民南迁,晋元帝将江南的几个县改封为琅邪郡以后,琅邪王的称号,在大江南北(包括滁州地区)广大臣民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时,才有可能按照琅邪王的称号,把属于淮南道的滁州的一座小山重名为“琅邪山”。关于这一点,前面引证的明万历《滁阳志》中记载的一段话,值得重视:“山何故因名,当元帝时,中国乱,元帝将渡江故避此,后既称帝,江表人即其故号为山名耳”。这里所说的“江表人”,是泛指今南京、江浦一带的本地人和山东南迁的“侨民”。虽然对晋元帝在渡江前是不是“避此”至今史学界有所争论,但滁州琅琊山这个名字,是在东晋时“江表人”首先口头命名的,这是一件历史事实。这正是唐代的滁州刺史李幼卿命名“琅琊山”、“琅琊溪”的根据。
纵观以上历史资料,我们总的看法是:滁州琅琊山名的由来,主要是因司马睿而命名,证据比较充分。但不能排斥或否定因司马伷而命名的说法,因为司马伷确实到过滁州,在平吴战争因吴主孙皓向他“送玺请降”立了大功,这也是历史事实。对历史上的这样一件大事,后代的地理著作和当地方志的撰写人会予以重视,以此来解释琅琊山名的由来。因此,我们认为,琅琊山名由来的两种说法,都是历史事实,不是“以讹传讹”的错误记载。从当时的整体形势推理,因司马睿而命名的根据更多,是主要的来源。作为志书,对由司马伷而命名的资料,也应全部记载,以让后代对这段历史有一全面的客观的了解。
最后,还有一个“琅邪王”和“琅琊山”的书写标准化的问题。根据史书的文字记载,自秦。汉至于晋代,无论地名、郡名、国名都写“琅邪”。唐代人编写的“晋书”,仍写为“琅邪王”、“琅邪郡”。“邪”在地名上使用时念yè(耶),不念邪恶的“邪”,也不念“牙”。滁州的琅琊山命名后,宋乐史编的《太平寰宇记》仍写“琅邪王”、“琅邪山”。宋代书法家苏轼写的题字和碑刻中,根据同音字写为“琅耶山”,直至清代和当代,不少地理著作仍写“琅邪王”、“琅邪山”。但至唐宋以来的大多数志书、游记、诗词,可能因口音不同,或是相互抄录,逐渐把“琅邪山”改写为“琅琊山”(琊字念“牙”),并用繁体字写为“
 玡山”、有的甚至把“琅邪王”,也改写为“琅琊王”,出现了一名多写的混乱情况。根据新编志书地名写法要规范统一的要求,在编纂新的《琅琊山志》时,我们根据滁州市地名办公室的规定,按照多年来的俗称,统一写为“琅琊山”,不写也不叫“琅邪山”、“琅耶山”,并按照国家文字机构颁布的简化字书写。至于“琅邪王”,应该照历史称呼书写,不能错写为“琅琊王”。这部新山志和这篇专文,只有在引证历史文献时,为保持原作的真实,原文怎样写就怎样写;由编纂者写的概述、大事记以及专文,则统一写为“琅邪王”、“琅琊山”,以避免一名多写的混乱现象。目前,全国各地还有几座同名山:河北省有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五壮士英勇抗敌的狼牙山;山东省有秦始皇到过的琅邪山;江苏南部句容县也有同名山。为了让全国的读者不棍淆地理概念,我们提议,在各地同名山的前面,加上所属省名,我们这座琅琊山电皤称叫“安徽省滁州琅琊山”。
玡山”、有的甚至把“琅邪王”,也改写为“琅琊王”,出现了一名多写的混乱情况。根据新编志书地名写法要规范统一的要求,在编纂新的《琅琊山志》时,我们根据滁州市地名办公室的规定,按照多年来的俗称,统一写为“琅琊山”,不写也不叫“琅邪山”、“琅耶山”,并按照国家文字机构颁布的简化字书写。至于“琅邪王”,应该照历史称呼书写,不能错写为“琅琊王”。这部新山志和这篇专文,只有在引证历史文献时,为保持原作的真实,原文怎样写就怎样写;由编纂者写的概述、大事记以及专文,则统一写为“琅邪王”、“琅琊山”,以避免一名多写的混乱现象。目前,全国各地还有几座同名山:河北省有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五壮士英勇抗敌的狼牙山;山东省有秦始皇到过的琅邪山;江苏南部句容县也有同名山。为了让全国的读者不棍淆地理概念,我们提议,在各地同名山的前面,加上所属省名,我们这座琅琊山电皤称叫“安徽省滁州琅琊山”。一九八八年五月
(韩枫,原任滁县地区编史修志办公室主任兼中共滁县地委党史办公室主任,现已离休。)
环滁皆山
江流
一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开头第一句就说:“环滁皆山也。”各种文集中对这一句话的注释,大都只说“环:环绕。滁:即滁州。”那么“皆山”又指哪些山?共有多少座山?却从未见有人具体注释过。据《朱子语类》第一三九卷称:“欧公文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原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可惜,我们今天连欧阳修原稿中概括叙述的“凡数十字”都已见不到,难怪一般注释家只好略而不谈了。
单说“环滁”的“滁”字,小而言之,仅指原来的滁县,即今日的滁州市,那么在它的东西南北四面,共有大小山头约七十座(详见附注)。如果大而言之,指宋代的滁州州治范围而言,它包括今天三个县以上的地区,那么其山峰的总数,就不是几十座,而是几百座了。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刊出了王俊坤的《“环滁皆山”小议》一文,编者在第一版把它列入“今日本报要目”。并赫然宣告说:“欧阳修观察有误,谬写‘环滁皆山,——请看第二版《‘环滁皆山’小议》。”·翻到第二版,《‘环滁皆山’小议》一开头就武断地说:
“到过滁州的人都知道,滁州除了城西和西北方向有山以外,东和东北方向皆不见山。欧阳公所谓‘环滁皆山’与事实不合。将一‘滁’的范围从州治所在地的滁城,扩大到整个滁州(包括现今滁县、来安、全椒三县),‘环滁皆山’还是得不到坐实。……所以‘环滁皆山’的描述有观察失真、概括失当之谬……使人颇感不解的是,自《醉翁亭记》间世九百余年来,赞美之词不绝于耳,却无人敢对其首句有所誉议”。接下去,还发了一大通议论,说什么“其一,读书应戴自己的眼镜”,其二,不必为名家、名篇讳言……应该旗帜鲜明地指出其谬误”云云,这里就无须多引了。
这位作者是否曾经乘车经过滁州车站,我自然无从断定。但可绝对肯定地说,他不仅没有到滁城周围实地看一看过,甚至连《滁州志》、《滁县乡土志》、《滁州市地名录》这一类最起码的现成资料,也根本没沾过边,却公然就“敢”“戴自己的眼镜”大发“訾议”,不仅“旗帜鲜明地”诬陷欧阳修“谬误”和“失真”,而且把“九百余年来”的读者一概骂倒。如此拿腔做调,信口雌黄,俨然“唯我独革”的文风,跟我们在“文革中司空见惯的那些所谓“革命大字报”的语气,何其相似乃尔!然而今天总不会再出现一个秦始皇,能挥起那根神话中的“赶山鞭”,把那些客观存在的山头,纷纷赶下海去吧?
二
博学多才的欧阳修,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单就舆地知识来说,从书本知识到感性知识,他都颇为渊博。他早年参加进士考试一举成名,考试题就是《司空掌舆地之图赋》,曾被主考官晏殊称赞说:“今一场举子,唯他一个人识题!”他当滁州太守后,也并非仅是常到“西南诸峰”之间去留连(他到滁州是被贬谪下来的,他自称“醉翁”,是佯狂诗酒,以掩权奸之耳目),实际上他是经常深入民间。滁州城东五里处有一菱溪,他就曾多次前去观察那里的石头,甚至引起群众的怀疑。他曾在诗中记述此事说:“溪边老翁生长见,凝我来视何殷勤。”这样的一位欧阳修,如果真的是城南、城东和东北方向“皆不见山”,他怎么诌出“环滁皆山”这一名句来呢?笑话!
地方建制沿革,常常是有变迁的。以宋代的滁州而言,其实也不仅是现在的滁州市(即原滁县)、全椒、来安三县的范围,它还包括现在嘉山县的一部分。嘉山是一九三二年新设的县,它的一部分就是由滁县、来安划出去的,例如原属滁县的张八岭,现在则属嘉山。滁州始置于隋,唐天宝初年改州为郡,以当时“州北三里”有永阳岭而命名为永阳郡。而这个永阳岭,如今则属来安县,在来安县城东偏北,距滁州市则有三十多华里。可见唐代和宋代之间,连州治的首府所在地也并不相同。
三
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其实不仅地方建制常有变迁,就连种种自然形态,也在不断地变异。一般地说,象山脉的情况,几百年间该不会有多少变化吧?其实不然。我们考核一下旧的《滁州志》,它初编于清康熙年间,最后重编于光绪年间,先后相距不过二百年左右。但在光绪年间重新编修时,就发现旧志中原有的十五座小山头,已经查访不着了!
滁州一带部分属山区,但多数则属丘陵地带。即以本文附注中所列的滁州市现有的七十座山为例,其中最高峰是北将军,海拔也还不到四百米;而象滁东赫赫有名的古迹皇道山,不过海拔数十米而已。这些低矮的小山和丘陵,是古淮阳山脉东翼的余脉,如果在我国山脉系统中论资排辈的话,它们称得上是老祖宗一辈。(至于目前世界最高峰所在的喜马拉雅山脉,从造山运动史的角度来衡量,它在山的庞大氏族中,只不过是少年儿童罢了。)但远古时代的大山,经过漫长历史世纪的不断侵蚀摧残,高度逐渐降低、有的甚至已成丘陵,也还有比丘陵被侵蚀得更厉害的准平原,实际上已经看不出“山”的任何面目来了。一九五六年我曾到嘉山县的平湖农庄访问(那里原属古滁州的范围之内),当时经勘察,那里土地中所含的砂石量,平均达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五点五。用拖拉机犁地,犁尖与翻土板的损耗率高得惊人。在夜间,拖拉机从地里开过时,遍地火星飞溅,那可以说正是“山魂”在显形。
在社会发展中,人口的变化也值得注意。翻开《宋史》来看,欧阳修时代的滁州人口,跟今天同一范围内的人口相比,当时的人口不过仅及今日人口的百分之六左右,地广而人稀。今日的低矮山包和丘陵,大都已化为农田和村落,而在昔日,则是树木荫森,虎狼出没,行为裹足,视为畏途,是道道地地的荒山和野岭。(明清时代一些著名的记叙文,对滁城附近老虎出没的具体形象和气氛都有记载。)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体味欧阳修所写的“环滁皆山”,才会更加形象逼真。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五日完稿
〔附注〕滁州市周围的山峦细列如下:
北有白米山、锅底山、牛牧岭、魏山岗、砂子岭、关山、棺材山。
东北有乌龙山、独山、大桂山、小桂山。
东有皇道山、姚大山、团山、林江墩。
东南有毛山。
南有大龙头、毛谷山、赵家大山、狐山、龙尾山、庙山。
西南有琅琊山、大丰山、鸡冠石、花山、绿豆山、菱角山、扁担山、庙山、狼头山、指马山、黄大山、宝塔山、江家山、妈蚁山、三百丈、凤凰山、杨梅山、瞌睡岭、炮楼山、南将军、老虎山、天尖山、尖山里、黑狼庙、滑鼻山、雁塘山、五尖山。
西有大尖山、团山、烟墩山、小红山、长山、皇甫寺(山)、相山、五斗山、磨刀石山、大山包、乌龟山、小磨盘山、小尖山之一、小尖山之二、宝塔山、烟龙包、狮子庙、张山尖、皇甫山、北将军、将军庙。
(江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安微省分会副主席。)
《醉翁亭记》碑文的几处考订
余炳华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我国文坛上著名的一篇散文。其韵味浓厚,诗情画意无穷,把琅琊山的风光描绘得绚丽多彩,引人入胜,实为古今中外人们喜读的好文章。由于这篇名著的问世,滁州琅琊山逐渐被历史名人所关注,招引不少名人来游,题咏琅琊山景色的文章,由古至今如泉涌而出。
多年来,国内不少文史工作者,常有著述描写醉翁亭,并附录《醉翁亭记》全文,或摘录其文名句,或是介绍它的意境和写作方法。但是,有些作者由于未能亲临其境,目睹其碑,以至把这篇名著的原文抄录错误。由于同样原因,有些出版部门的编者,难以识别错处,将抄录有错的《醉翁亭记》正式编入书刊,广泛流传社会,使读者曲解此文的意境,降低此文的历史价值。翻为滁州的文史工作者,虽未亲眼见过欧阳修自书的《醉翁亭记》碑刻,而对苏轼所书的《醉翁亭记》碑刻却随时可以拜读(苏轼书写的碑刻现仍在滁州市醉翁亭的宝宋斋内)。由于沧桑变迁,此碑已经剥脱不全。多年来,我搜集了一些版本的《醉翁亭记》碑帖,按照原碑一一作了校订,发现中华书局1982年6月出版的《古文观止》中《醉翁亭记》错字较多,丢字、错字和错句竟达十三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的《欧阳修》一书,原文照录的《醉翁亭记》,有六个错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的《欧阳修》所附录的此记,也有六个错字。除此而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的《醉翁亭记》帖本,可以算是目前最好的版本了。但是,其中的序和抄本也有三处差错。
对于《醉翁亭记》这篇文章,我们应该视作民族文化遗产,要保存其原貌,不应在引用时改变其原文,以免贻误我们对欧阳修诗文的研究。
对于原文中“让泉”的“让”字,不应误用“酿”字;“水清而石出”的“清”字,不应误用“落”字;“莫而归”的“莫”字,在此文中虽然可以作为“暮”字用,如果作为原文引用,则应该用“莫”字。为了方便读者,可以在“莫”字后面写个“(暮)”,以作注释。“负者歌于途”的“途”字,不应误用“涂”和“塗”字。“太守燕也”、“燕酣之乐”两处的“燕”字,在这里就是“宴”字的代用字,也用上述方法处理。“坐起而喧哗者”的“坐起”二字,原碑实为“起坐”。原碑跋文中有“字画浅褊”,而光绪二十三年版本的《滁州志》却误为“字画褊浅”。对以上诸问题,我们应该正确订正,而出版部门,更需要认真以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碑帖进行校核。这样,才能保证这篇名著原原本本地流传于世。
(余炳华,现任滁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